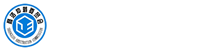2025 年 9 月,第十四屆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表決通過(guò)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仲裁法》,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標(biāo)志著我國(guó)仲裁制度迎來(lái)歷史性變革。此次修訂在仲裁協(xié)議效力認(rèn)定、仲裁地選擇、臨時(shí)仲裁制度等方面實(shí)現(xiàn)重大突破,立法機(jī)關(guān)明確將“提升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作為核心目標(biāo),要求仲裁事業(yè)“服務(wù)國(guó)家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高水平對(duì)外開(kāi)放”。
仲裁員資質(zhì)門檻的實(shí)質(zhì)提高
從"資格條件"到"素質(zhì)操守"的全面升級(jí) 舊《仲裁法》第22條僅以"公道正派"為核心要求,列舉了仲裁、律師、審判員等五類職業(yè)背景條件,未明確專業(yè)素質(zhì)與職業(yè)道德標(biāo)準(zhǔn)。2025年修訂的新法第22條則實(shí)現(xiàn)三大突破:一是強(qiáng)化資質(zhì)剛性約束,要求法律類仲裁員需"通過(guò)國(guó)家統(tǒng)一法律職業(yè)資格考試";二是擴(kuò)展專業(yè)領(lǐng)域覆蓋,將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貿(mào)易"擴(kuò)展至"海事海商、科學(xué)技術(shù)等",吸納跨學(xué)科專家,例如上海國(guó)際仲裁中心在2024年啟用的新版《仲裁員名冊(cè)》增設(shè)《航空爭(zhēng)議》《數(shù)據(jù)爭(zhēng)議》特別名單,凸顯對(duì)細(xì)分領(lǐng)域?qū)<业尼槍?duì)性需求;三是突出職業(yè)倫理要求,首次明確仲裁員需"具備良好的專業(yè)素質(zhì),勤勉盡責(zé),清正廉明,恪守職業(yè)道德",從立法層面構(gòu)建"能力+操守"雙重門檻。同時(shí),新法規(guī)范公職人員兼任行為,明確《監(jiān)察官法》等禁止性規(guī)定,并允許聘任"具有專門知識(shí)的境外人士",體現(xiàn)國(guó)際化開(kāi)放態(tài)度。當(dāng)然,新《仲裁法》也明確新增"曾任檢察官滿八年"的任職路徑,為曾經(jīng)在檢察系統(tǒng)工作多年的專家充實(shí)到仲裁員隊(duì)伍中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jù)。 新法通過(guò)"法律職業(yè)資格前置+專業(yè)領(lǐng)域擴(kuò)展+職業(yè)道德法定化"三重路徑,配合境外人才開(kāi)放與動(dòng)態(tài)審查機(jī)制,推動(dòng)仲裁員資質(zhì)從"經(jīng)驗(yàn)導(dǎo)向"向"專業(yè)能力與職業(yè)倫理雙達(dá)標(biāo)"轉(zhuǎn)型,為提升仲裁公信力奠定人才基礎(chǔ)。 披露義務(wù)與獨(dú)立性要求的強(qiáng)化 仲裁員的披露義務(wù)與獨(dú)立性是仲裁程序公正性的核心保障,司法實(shí)踐已通過(guò)典型案例明確其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指出,仲裁員若未書面披露可能引發(fā)對(duì)其獨(dú)立性或公正性合理懷疑的事項(xiàng),可能因“不具備資格”導(dǎo)致委任自動(dòng)終止。 新《仲裁法》從制度層面強(qiáng)化了相關(guān)要求。第21條明確仲裁員需“公道正派,具備良好的專業(yè)素質(zhì),勤勉盡責(zé),清正廉明,恪守職業(yè)道德”,為獨(dú)立性要求奠定法律基礎(chǔ)。進(jìn)一步建立信息公開(kāi)和披露制度,要求仲裁員主動(dòng)披露可能影響其獨(dú)立性、公正性的相關(guān)信息,以消除信息不對(duì)稱。 國(guó)際層面,英國(guó)《2025年仲裁法》的修訂為披露義務(wù)提供了更精細(xì)化的參照。該法將仲裁員的普通法披露義務(wù)法典化,明確其為持續(xù)性義務(wù),涵蓋仲裁員已知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的、可能合理引發(fā)對(duì)其公正性產(chǎn)生懷疑的所有情形,且義務(wù)擴(kuò)展至任命前的討論階段。新增的第23A條進(jìn)一步規(guī)定,披露義務(wù)屬于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當(dāng)事人不得約定免除,“相關(guān)情況”包括可能使人對(duì)其公正性產(chǎn)生合理懷疑的所有情形,仲裁員“應(yīng)當(dāng)合理知悉的情況將被視為已經(jīng)知悉”。這種“強(qiáng)制性+持續(xù)性”的披露標(biāo)準(zhǔn),與中國(guó)通過(guò)“公道正派”“清正廉明”等原則性要求強(qiáng)化獨(dú)立性的路徑形成對(duì)比,反映了不同法域在平衡靈活性與確定性上的制度選擇。 無(wú)論是中國(guó)通過(guò)立法原則與行為守則的協(xié)同強(qiáng)化,還是英國(guó)以法典化方式細(xì)化披露標(biāo)準(zhǔn),均體現(xiàn)了仲裁員獨(dú)立性與披露義務(wù)的嚴(yán)格化趨勢(shì)。這一趨勢(shì)不僅回應(yīng)了“消除信息不對(duì)稱、增強(qiáng)仲裁公信力”的現(xiàn)實(shí)需求,也為跨境商事糾紛解決提供了更可預(yù)期的程序保障。 臨時(shí)仲裁程序管理能力的新挑戰(zhàn) 傳統(tǒng)仲裁程序中,由機(jī)構(gòu)及秘書處主導(dǎo)程序的啟動(dòng)和推進(jìn),仲裁庭的主要職責(zé)在于組庭后的對(duì)案件實(shí)體內(nèi)容的審理,包括法律問(wèn)題及事實(shí)問(wèn)題等。仲裁庭對(duì)于程序事項(xiàng)的安排空間相對(duì)有限,主要在庭后提交材料的期限以及逾期提交的處理結(jié)果,以及是否接納過(guò)遲提出的補(bǔ)充仲裁請(qǐng)求或仲裁反請(qǐng)求等。當(dāng)然,如何處理這些程序性事項(xiàng),不同的仲裁庭之間也相對(duì)比較一致,一般而言仲裁庭更傾向于尊重意思自治,保障當(dāng)事人合法發(fā)表觀點(diǎn)的權(quán)利為主。除非明顯有拖延程序仲裁裁決效率和公正性的可能,一般來(lái)說(shuō)仲裁庭不會(huì)簡(jiǎn)單拒絕當(dāng)事人提交書面材料。 而在臨時(shí)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則被賦予了更多的權(quán)限去主導(dǎo)程序節(jié)奏,制定程序規(guī)則,舉證期限,庭審安排等節(jié)點(diǎn)。 仲裁員們需注意,程序自主約定并非“放任自由”,需結(jié)合案件特點(diǎn)選擇第三名仲裁員選任方式(仲裁員共同選定、當(dāng)事人共同選定或指定),在“靈活”與“規(guī)范”間找到平衡。臨時(shí)仲裁制度的落地對(duì)仲裁員的程序駕馭能力提出系統(tǒng)性重構(gòu)要求,其核心矛盾在于“高度自主的程序設(shè)計(jì)”與“剛性時(shí)限約束”的平衡。根據(jù)新《仲裁法》第82條,仲裁庭需在組庭后3個(gè)工作日內(nèi)向仲裁協(xié)會(huì)完成備案,內(nèi)容涵蓋當(dāng)事人名稱、仲裁地、仲裁庭組成及仲裁規(guī)則等核心要素;而實(shí)務(wù)中可能需要涵蓋的內(nèi)容更多,可能還需要包括仲裁庭的職業(yè)簡(jiǎn)歷及背景、利益沖突查詢結(jié)果、仲裁庭預(yù)判的裁決期限等等。這對(duì)仲裁員的組庭效率與規(guī)則熟悉度構(gòu)成直接考驗(yàn)。 程序主導(dǎo)權(quán)的轉(zhuǎn)移是另一重挑戰(zhàn)。與機(jī)構(gòu)仲裁不同,臨時(shí)仲裁中仲裁庭需獨(dú)立承擔(dān)“案件管理會(huì)議召集”“程序令簽發(fā)”“證據(jù)規(guī)則適用”“臨時(shí)措施決定”等全流程職責(zé),典型如“區(qū)分仲裁通知與仲裁申請(qǐng)書”的實(shí)踐模式,需仲裁員主動(dòng)推動(dòng)當(dāng)事人參與程序框架設(shè)計(jì)。 這就要求仲裁員具備“效率-合規(guī)”雙效的把控,通過(guò)預(yù)編全流程節(jié)點(diǎn)表(含證據(jù)交換、庭審、裁決時(shí)限)。 國(guó)際視野與規(guī)則適用能力的拓展 新《仲裁法》明確了“仲裁地”這一學(xué)術(shù)概念,明確其作為程序適用法、裁決國(guó)籍及司法管轄的核心依據(jù),標(biāo)志著中國(guó)仲裁制度與國(guó)際實(shí)踐的深度接軌。當(dāng)事人選擇“上海為仲裁地、適用UNCITRAL規(guī)則”,或者當(dāng)事人約定仲裁地(不排除出現(xiàn)類似于上海為仲裁地、中國(guó)香港為開(kāi)庭地)及國(guó)際通行規(guī)則,可能會(huì)慢慢出現(xiàn)并在一定范圍內(nèi)稱為主流范本。這就要求仲裁員具備跨規(guī)則適配能力,需快速切換對(duì)組庭機(jī)制、證據(jù)開(kāi)示等條款的理解。 實(shí)踐中,仲裁員很可能應(yīng)對(duì)多元挑戰(zhàn):如案件當(dāng)事人從約定LCIA規(guī)則轉(zhuǎn)為適用上海的規(guī)則,考驗(yàn)跨規(guī)則切換能力。證據(jù)收集環(huán)節(jié),新法第55條賦予仲裁庭自行收集證據(jù)以及請(qǐng)求“有關(guān)方面”依法協(xié)助的權(quán)力,突破舊法下調(diào)查權(quán)局限。因此仲裁庭可能還需要在庭審或者聽(tīng)證過(guò)程中擬定調(diào)查提綱,必要時(shí)申請(qǐng)法院,甚至可能是境外法院,出具調(diào)查令或者披露命令等。 此外,AI技術(shù)(如HKIAC的Jus AI案例摘要系統(tǒng))與跨境數(shù)據(jù)流動(dòng)合規(guī)(如中國(guó)“封阻法令”對(duì)證據(jù)交換的限制),進(jìn)一步要求仲裁員兼具技術(shù)適配與法律協(xié)調(diào)能力。 聯(lián)合國(guó)貿(mào)法委指出,現(xiàn)代仲裁員需“在本土實(shí)踐與國(guó)際規(guī)則間建立動(dòng)態(tài)平衡”,這要求仲裁員們既需熟悉《紐約公約》對(duì)裁決承認(rèn)的核心要求,又要靈活運(yùn)用不同法域程序規(guī)則,方能滿足全球當(dāng)事人對(duì)爭(zhēng)議解決的復(fù)合型需求。 仲裁員能力體系的三維構(gòu)建 新《仲裁法》實(shí)施后,仲裁員可能需要從傳統(tǒng)的德高望重公平公正的法律專家,向具備三重能力體系的專業(yè)化法律服務(wù)人才轉(zhuǎn)型。這一體系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獨(dú)立性與職業(yè)倫理維度,強(qiáng)化披露義務(wù)與聲譽(yù)管理;二是專業(yè)與程序管理維度,涵蓋國(guó)際公法知識(shí)、臨時(shí)仲裁程序設(shè)計(jì)及高效案件推進(jìn)技能;三是國(guó)際視野與包容性維度,要求具備跨境爭(zhēng)議解決經(jīng)驗(yàn)、地域與法系代表性及多元利益協(xié)調(diào)能力。仲裁員需深度掌握包括《聯(lián)合國(guó)國(guó)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huì)示范仲裁規(guī)則》等國(guó)際“軟法”與中國(guó)仲裁法的沖突解決路徑。 此外,新《仲裁法》第94條明確支持仲裁機(jī)構(gòu)辦理國(guó)際投資仲裁案件,因此,除了類似于律師行業(yè)的“雙語(yǔ)辦案”和“基于跨境證據(jù)的事實(shí)查明”等復(fù)合能力,對(duì)于仲裁員來(lái)說(shuō),還需要具備足夠的國(guó)際公法領(lǐng)域的知識(shí)儲(chǔ)備,對(duì)于域外法律和國(guó)際條約的查明具有相當(dāng)專業(yè)的要求。關(guān)于這方面,我們也在積極朝國(guó)際公法和國(guó)際經(jīng)濟(jì)法律方向進(jìn)行轉(zhuǎn)型,增加理論研究和案例儲(chǔ)備。同時(shí)仲裁員在國(guó)際投資案件中,也一定程度上要更多參考國(guó)際律師協(xié)會(huì)《國(guó)際仲裁行為準(zhǔn)則》中的保密義務(wù)與利益沖突披露規(guī)范。 新《仲裁法》的實(shí)施雖意義重大,但落地過(guò)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zhàn)。 首先,"仲裁地"的確定規(guī)則需細(xì)化。新法規(guī)定"仲裁地"遵循"當(dāng)事人約定—仲裁規(guī)則規(guī)定—仲裁庭確定"的優(yōu)先順序,但實(shí)踐中,如何界定"仲裁規(guī)則規(guī)定"仍存爭(zhēng)議。其次,特別仲裁的適用范圍需謹(jǐn)慎界定。新法將特別仲裁限定于"涉外海事糾紛、自貿(mào)區(qū)企業(yè)涉外糾紛",但"自貿(mào)區(qū)企業(yè)"的界定、"涉外"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仍需司法解釋明確。 第三,臨時(shí)仲裁的監(jiān)管機(jī)制需完善。臨時(shí)仲裁雖賦予當(dāng)事人更大自主權(quán),但也可能引發(fā)仲裁程序不規(guī)范、仲裁員資質(zhì)存疑等問(wèn)題,需建立配套的監(jiān)管機(jī)制。 盡管如此,新《仲裁法》的施行標(biāo)志著中國(guó)仲裁從“貿(mào)易大國(guó)”爭(zhēng)議解決機(jī)制向“規(guī)則大國(guó)”制度輸出載體的戰(zhàn)略轉(zhuǎn)型。在此背景下,仲裁員能力體系的重構(gòu)需以角色轉(zhuǎn)型為核心,通過(guò)三維能力的動(dòng)態(tài)平衡回應(yīng)新時(shí)代要求。正如聯(lián)合國(guó)貿(mào)法委秘書長(zhǎng) Anna Joubin-Bret 所評(píng)價(jià),“中國(guó)仲裁法修訂為發(fā)展中國(guó)家提供了制度創(chuàng)新的范本”,而仲裁員能力體系的成熟度,將直接決定中國(guó)仲裁在全球爭(zhēng)議解決格局中的話語(yǔ)權(quán),成為“中國(guó)方案”走向世界的關(guān)鍵橋梁。 來(lái)源:企鵝大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