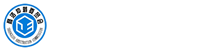2025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了第五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案例。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5批45個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案例,其中涉及仲裁的典型案例共有8個,為便于大家學習,特將相關仲裁案例整理如下。
第一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仲裁案例 尊重當事人仲裁意愿 推動仲裁國際化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與盧森堡英威達技術有限公司申請確認仲裁條款效力案(2014年) 【典型意義】 該案首次認可當事人約定由中國的常設仲裁機構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管理仲裁程序的條款效力,并明確該條款約定的是機構仲裁,而非臨時仲裁。該案對當事人理解存在分歧的合同用詞,采取了有利于實現當事人仲裁意愿的目的解釋方法,在仲裁條款未明確限定仲裁機構特定職能的情形下,認定當事人關于常設機構適用另一仲裁規則的約定應理解為該機構依仲裁規則管理整個仲裁程序。本案對于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支持仲裁國際化、提升仲裁公信力,具有典型示范意義。 第二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仲裁案例 恪守《紐約公約》裁決執行義務 營造自貿試驗區優質法治環境 ——西門子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與上海黃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 【典型意義】 自貿試驗區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平臺、重要節點和戰略支撐。接軌國際通行做法,支持自貿試驗區發展、健全國際仲裁以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有助于增強中國法治的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本案裁定在自貿試驗區推進投資貿易便利的改革背景下,對自貿試驗區內外商獨資企業之間的合同糾紛,在涉外因素的認定方面給予必要重視,確認仲裁條款有效,并明確“禁止反言”,踐行了《紐約公約》“有利于裁決執行”的理念,體現了中國恪守國際條約義務的基本立場。同時,該案由點及面推動了自貿試驗區內企業選擇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自貿試驗區可復制可推廣司法經驗的一宗成功范例。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規定自貿試驗區內注冊的外商獨資企業相互之間約定將商事爭議提交域外仲裁的,不應僅以其爭議不具有涉外因素為由認定相關仲裁協議無效;并規定一方或者雙方均為在自貿試驗區內注冊的外商投資企業,約定將商事爭議提交域外仲裁,一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域外仲裁,在相關裁決做出后又主張仲裁協議無效,或者另一方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對仲裁協議效力提出異議,在相關裁決做出后又以不具有涉外因素為由主張仲裁協議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有助于構建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一帶一路”法治化營商環境。 第三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仲裁案例 明晰仲裁裁決籍屬認定規則 明確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作出的裁決視為涉外仲裁裁決 ——美國布蘭特伍德工業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 【典型意義】 該案經報核至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首次明確了境外仲裁機構在我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籍屬的認定規則,將該類裁決視為我國涉外仲裁裁決,確認該類裁決能夠在我國內地直接申請執行,有利于提升我國仲裁制度的國際化水平,樹立了“仲裁友好型”的司法形象,對于我國仲裁業務的對外開放及仲裁國際化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第四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仲裁案例 案例一 依法駁回案外人執行異議訴請,及時有效執行外國仲裁裁決 ——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與俄羅斯薩哈林海產品無限股份公司、東方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 【典型意義】 本案外國仲裁裁決經人民法院裁定承認,并在裁定執行過程中查封了案涉財產,而被執行人通過轉讓被查封財產、提起另案訴訟對查封財產進行確權等方式意圖規避執行。人民法院依法執行外國仲裁裁決,不僅駁回執行異議申請,并在其后的執行異議之訴中,根據司法解釋規定,認定受讓行為并非善意,同時及時對生效的另案確權判決予以再審,體現了我國法院為保障仲裁裁決跨境執行而采取的各項有效舉措,有力維護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 案例二 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 依法保護“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企業合法權益 ——來寶資源國際私人有限公司(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 Ltd.)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裁決案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中國企業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企業之間發生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經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后,外國企業向我國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本案中涉及“多份合同、單個仲裁”,人民法院依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審查認定仲裁程序的合法性,有效維護了仲裁當事人的正當程序權利。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香港的國際仲裁機構成為“一帶一路”項目糾紛當事人經常選擇的爭議解決平臺之一。本案根據內地與香港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依法認可和執行案涉裁決,為當事人在港解決“一帶一路”糾紛提供了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第五批涉“一帶一路”建設典型仲裁案例 案例一 準確界定中蒙雙邊條約范圍 依法承認和執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仲裁裁決 ——蒙俄合資有色金屬國有企業與西洲(上海)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 【典型意義】 案例二 構建全鏈條國際商貿爭端解紛模式 助力中外企業修復關系“和合共贏” ——Agerratum有限責任公司與特思味(廈門)食品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涉金磚國家外國仲裁裁決案 【典型意義】
蒙古國系“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共建國家之一,中蒙兩國長期保持著頻繁的經貿往來。我國和蒙古國雖然簽訂《中蒙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但僅包括民事裁判的相互承認和執行的內容,未規定仲裁裁決的相互承認和執行。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海國際商事法庭)根據條約解釋的相關規則,準確認定《中蒙雙邊司法協助條約》所涉“主管機關”不包含仲裁機構,進而明確應依據《紐約公約》對案涉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問題進行審查。本案厘清了《紐約公約》和《中蒙雙邊司法協助條約》的關系,明確了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申請承認和執行蒙古國仲裁裁決的審查依據。本案的高效審結,有效增進了國際經貿、人員往來的互信基礎,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司法協助水平。同時,本案對于準確適用國際規則、全方位服務保障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高效率地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已成為評價一國營商環境是否良好的重要標志。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一是全面準確適用《紐約公約》。進一步明確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審查標準,厘定“適當通知義務”,切實踐行《紐約公約》“有利于仲裁執行”理念,展現了我國遵守國際公約的契約精神;二是體現專業化、國際化水平。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廈門國際商事法庭)選擇熟悉金磚國家商貿規則的人民陪審員組成本案合議庭,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內依法高效審結案件,并且當庭裁定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三是構建全鏈條國際商貿爭端解紛模式。法庭在當庭裁定承認和執行案涉外國仲裁裁決后,又出具執前督促履行義務通知書,實現與執前調解的有機銜接,促使中外當事人當庭達成和解協議,助力修復雙方經貿關系,以個案的小切口,為“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提供實踐范本,促進金磚經貿合作的軟聯通。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